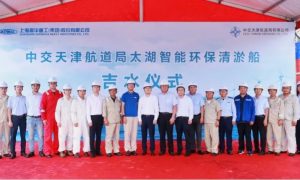圖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四庭審判長余曉漢
各位老師、同事們,下午好!今天下午在有限的幾分鐘時間內,我準備主要談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個人基本觀點;二是對這次會議的感想。
我的基本觀點是:我明確地反對將內河船舶和內河運輸納入《海商法》,也反對將港口作業合同作為一章一節地納入《海商法》。我也基本上不贊同對于《海商法》修改,在章節上進行調整和變動。《海商法》修改應以第四章為重點,其他章節稍微做些修改即可。這個問題,我今天可以做一個大膽預測:我們今天準備對《海商法》大修大改,討論得轟轟烈烈,但將來立法最終修改很可能是簡簡單單。修法一般是直接針對法律的哪條哪款做簡單明了的修改,不輕易在結構體例上變動,一般也沒有大篇幅地條文修改,基本上沒有見到哪一部法律的修改像我們這樣討論修改《海商法》一樣大修大改。
剛剛社科院法學所莫紀宏老師的講話很有啟發性和針對性,我認為他的講話強調了三點內容即法律普遍性、成長性、實效性。這個會議在社科院開,它的高度、視野確實不一般,這個會議在這里召開有特殊意義。對于這個特殊意義,今天由于時間所限,我就不展開談了。今天我也不談其他內容,主要談反對將內河運輸和內河船舶納入《海商法》的意見和部分理由(有的理由比如國際海上貨物運輸與內河運輸制度的歷史淵源等,今天不談,主要談其中一二點)。
我的理由:我之所以明確反對將內河船舶和內河運輸納入《海商法》,首先從修法的實效性看,可以預測將內河船舶和內河運輸納入《海商法》的實際效果會很差。它解決的問題是有的,但是制造的麻煩一定比它解決的問題要多。這就像一些西方學者對《鹿特丹規則》的評價一樣。對于《海商法》修改是否將內河運輸和內河船舶納入的問題,我在原來(大連)開會的時候主張如果能夠明確將來修改后的《海商法》所調整的內河范圍和內河船舶范圍,則可以考慮修法納入,如果不能明確上述范圍并以事實和數據充分論證,則不能盲目納入。到現在,沒有人能明確《海商法》擬調整內河和內河船舶的范圍并充分論證,所以我明確反對。考慮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僅看長江干流,也不能僅看黑龍江、長江、珠江這三大通航能力較強的水系,要摸清全國所有通海可航內河的情況,我們中國有5800多條河流,內河總長43萬公里,約四分之一通航(約10萬公里);我國通海可航的內河情況比較復雜,包括黃河、淮河、京杭大運河、閩江以及南方的水系,黃河有時候通航有時候(部分河段封凍和枯水期)不通航,所有這些內河的通航情況(包括干流與眾多支流)現在仍說不清楚。如果《海商法》修改將內河運輸和內河船舶納入調整范圍,《海商法》及其相配套的《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將在全國范圍內更加廣泛地實施。就法院而言,除海事法院經常適用外,其他人民法院也將經常或者偶爾適用。如果某些法院經常適用,則可積累經驗確保專業水平;但如果僅偶爾適用則效果就難以保障。《海商法》和《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中海事賠償責任限制基金設立、船舶優先權等特殊制度如果將來在地方法院不時需要適用,則情況難料,估計相當長時期內全國會存在《海商法》和《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應當適用而沒有適用等突出問題。如果《海商法》將內河運輸和內河船舶納入其中,為了便于其全面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修訂時應當一并修改名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上與內河運輸法”,否則不必說一般人民群眾,就是一般的律師、法官也未必就理所當然地知道《海商法》也調整內河運輸和內河船舶,很可能大家顧名思義地認為《海商法》就是調整海上商業活動的。盡管理論上說“海事”包括內河甚至湖泊中發生的事,但社會實踐中的一般性或者常識化認知卻并非如此。所以,我們如果考慮將內河運輸和內河船舶納入《海商法》,就應當一并修改法律名稱,做到名實相符,克服名實不符的問題。法律名稱包括其內部章節的標題做到名實相符很重要,就以現在《海商法》第四章的名稱為“海上貨物運輸”而言,該法實施25年了,時間不短,而且還有專門化的海事審判機構體系予以保障,但僅我一人就在近幾年的裁判文書中發現有一個海事法院和三個高級人民法院的裁判文書在國內沿海運輸合同糾紛中援用《海商法》第四章的規定(盡管裁判結果均并無不當),如果大家全面檢索可能會發現更多類似情況。對于上述問題,我以前總是責怪我們法官群體存在人員流動頻繁、自身學習不足等專業維持不夠問題,但現在看來《海商法》第四章的名稱“海上貨物運輸”與其僅調整國際海上貨物運輸的內涵之間的差異也的確很容易讓人產生錯誤認識。法律名稱及其內部章節做到名實相符,可以為人們遇到法律問題時準確“找法”大大提供方便,反之則不盡然,上述教訓可見一斑。
其次,就法律的普遍性而言,《海商法》現在除調整海上運輸并調整江海直達運輸外,不調整內河運輸和內河船舶,也沒有專門港口貨物作業的章節,是不是內河運輸和港口經營就無法可依呢?我根本不同意哪些無法可依的說法,內河運輸和港口經營難道不在民法總則(以前民法通則)、物權法、合同法、侵權責任法等民事基本法的調整范圍內嗎?這不是無法可依,實際上是沒有特別保護某些特定主體(行業)所企求特殊利益的一個特別法,僅此而已。說無法可依顯然是一個偽命題。要求將內河運輸和內河船舶納入《海商法》的主張,核心要求:一是主張內河船舶適用船舶優先權制度以解決內河船員報酬被拖欠后的清償問題;二是主張內河運輸適用國際海上貨物運輸中的承運人免責與責任限制規定和內河船舶經營適用海事索賠責任限制制度,以特殊保護內河船舶運輸行業。從歷史淵源看,《海商法》從維護國際海上運輸規則的國際統一性出發,充分吸收借鑒國際條約規定和國際習慣做法,規定包含部分傾向保護海上運輸業的特殊規定,的確有其制度演變與傳承上的歷史與國際因素;而內河運輸基本上沒有這些歷史與國際因素。主張將內河運輸和內河船舶納入《海商法》的意見,主要是出于在立法上尋求特殊保護內河運輸業的現實利益驅動。公平地看,法律上給予內河運輸業特殊保護,就是要求內河運輸的服務對象(貨主和旅客)為此作出特殊犧牲或者利益讓步,這是現實的利益分配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內河運輸的服務對象(貨主和旅客)就“該死”嗎?應當看到,內河運輸與之服務的經濟貿易發展而言,相對程度上是手段與目的的關系(不排除運輸經濟的相對獨立性),內河運輸的服務對象(貨主和旅客)“該死”,內河運輸就“該活”嗎?我必須再強調內河運輸與國際海上運輸法律上不可比主要在于制度的歷史淵源不同。這個現實的正義分配問題,要改變現行法律主旨即《海商法》的初心(調整海上運輸,重點是國際海上運輸)必須要有充分論證,僅內河運輸業僅僅強調保護其利益的重要性顯然不夠,甚至有行業自利之嫌。公平公正地看,我們還必須始終留意一個現象:海運和內河運輸業好比“機構投資者”,有專門、持續、強大的代言群體;而廣大貨主和旅客一個個處于“散戶”,難以組成統一、有力的發聲力量。這也是立法分配正義時值得特別關注的問題,某個行業僅說自己重要并不足信。除了充分論證立法分配正義的理據外,還要考慮內河運輸業提出的問題是否可以通過其他方式方法解決?非得通過修改《海商法》不可嗎?比如,內河船員報酬被拖欠的清償問題,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工資等勞動勞務報酬優先受償,行政法規還可以規定要求內河船舶經營者提供船員勞動勞務報酬擔保金制度(如無船承運人擔保金制度),也可以規定行政處罰措施等等;《海商法》規定的承運人免責和單位責任限制、海事索賠責任限制等特殊制度相當程度上是國際上歷史遺留問題,如果沒有歷史遺留,就現行經濟發展和法律制度,船舶經營的風險可以通過提高運費并相應增加保險、行業內互保等社會化方式解決,最多保留一個相當高的一般不易觸及的事故賠償限額即可。目前,對于內河運輸的問題是否非得通過修改《海商法》來解決,也遠遠沒有說清楚。退一步考慮,如果內河運輸確有必要專門立法規制,還可以提議制定“內河運輸法”。
我反對將內河運輸和內河船舶納入《海商法》的態度,一是明確;二是堅決。剛才我說了明確反對的理由。接下來,我要說為什么要堅決反對。《海商法》修改將內河運輸和內河船舶納入沒有相對充分的理據,提議納入會牽一發而動全身,簡單說就是“攪局”,這么一“攪局”后面很多事情都會被掣肘、被拖累,嚴重影響修法研究進程。就像寫一篇文章,如果基本問題定不下來,框架和具體內容沒有辦法順利展開。盡管部分同志對提議將內河運輸和內河船舶納入《海商法》,付諸了很大熱忱和努力,我也深受感染到幾乎認同,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時間越來越接近我們必須理性思考并作出果斷決定的時候,我認為當務之急就是首先干凈利落地將內河運輸和內河船舶從《海商法》修改議程中刪除,便于《海商法》修改“丟下包袱,輕裝上陣”,著力解決好自身問題和重點問題。簡而言之,《海商法》修改到了對內河運輸和內河船舶納入果斷說“不”的時候了。以上個人意見,供大家商討。
來源: 海商法研究中心 余曉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