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榮生(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船舶工業行業協會會長,原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總經理)口述
于洋整理
三線船舶工業的舊貌新顏
 王榮生
王榮生
在新中國船舶工業發展史上,三線建設可以說是濃墨重彩的一筆,它對產業布局所產生的影響相當深遠。
傳統船舶工業的分布,我們習慣上叫“三點一線”:上海一片,東北一片,廣東、廣西有一片,還有長江這一條線。20世紀60年代初,隨著毛主席、黨中央一聲令下,“好人好馬上三線”。船舶工業幾十個工廠、研究所的上萬名職工從大連、上海、武漢、洛陽等大城市,奔赴四川、云南、陜西、湖北的一些崇山峻嶺,在那里安營扎寨,深挖洞、散建房,硬是在荒山僻嶺中建起了一座座現代化的工廠和科研所。邊建設,邊生產,一條條潛艇、一艘艘水面艦艇、一臺臺柴油機、一只只儀器儀表從這里被敲鑼打鼓地送出來,為海軍現代化建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其創業之艱辛,生活之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但當時沒有人叫苦,沒有人埋怨。
我真正搞三線工作是1982年5月4日成立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以后。那時我進了部里,到了領導崗位上,負責進行三線建設的調整、改造、整頓。1983年—1986年這幾年的任務比較重,工作開展起來相當艱難。改造結束,大概要到90年代。
 三線調整改造時期,王榮生(右一)在水中兵器廠車間現場看工人師傅制造精密零件
三線調整改造時期,王榮生(右一)在水中兵器廠車間現場看工人師傅制造精密零件
三線調整開始以后,有人說我們是搞了重復建設,但實際上絕不是這樣。由于造船的復雜性,對船廠的要求更多一些,因此一部分船廠確實是需要調整的。究竟怎么辦,我就搞了一個規劃。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對涉及的企業和研究所的處理分為“關、停、并、轉”這么幾類。意思是有的要關閉,有的要停辦,有的要兼并,有的要轉行。具體怎么處理,我們會根據實際情況來定。各個單位的情況也是五花八門的:有的廠沒有形成生產力,實在建不下去,就把它撤了;有的雖然已經形成了生產力,但是產品不配套,就停工了;有些研究所交通不便,要想辦法把它遷出來,特別是現在電子技術發展以后,科研人員帶著控制設備、儀表這一套東西進去,太不現實;但已經建好的,像是潛艇廠則只能堅持在原地,因為水工基礎沒法搬;有的則轉成生產跨行業產品的廠家。
我們曾有一片都是以軍為主的船廠,有搞護衛艦的,有搞快艇的,有搞潛艇的,有搞大型的水面艦艇的,等等。現在這部分船廠也進行了必要的搬遷和調整。比如,現在的江蘇科技大學附近原來有一個快艇廠,從產品來看,快艇發展蠻慢的,我們就把原來的生產人員和設備都交給學校,跟它合并了起來,實際上就等于把這個廠給撤銷了。像某通信研究所,我們從深山里面把它遷出來以后,帶到連云港,建了一個實驗基地,這樣,陸上有火車,也有汽車,交通就方便多了。某柴油機研究所在三線建設的時候,從上海遷到了山溝,調整改造時期又遷回了上海,在山溝里的所址則交給了地方。還有個快艇主機廠,我們考慮到重型汽車的發動機和快艇的發動機是通用的,就讓它跟濰坊重汽的柴油機生產廠家聯合起來。于是,山東想辦法劃給了它一塊地,這個廠就保持了生產能力,但屬于山東汽車工業公司,實現了軍民結合。而某潛艇廠生產結構得到了調整,不光造潛艇,還造一些特種船、化學品船,等等。這都是做得比較好的,對國家貢獻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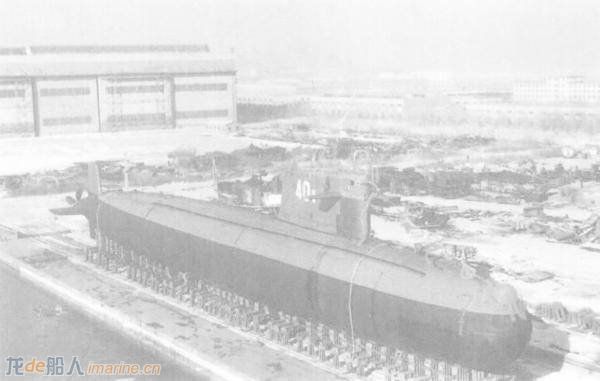 我國第一艘核潛艇
我國第一艘核潛艇
對于中國船舶工業來說,三線建設具有很重大的積極意義。三線建設的貫徹落實,對于中國船舶工業的發展,是不可缺少的。我們一直講,不要把三線企業看成是包袱,將來是可以發揮作用的。現在看來,三線建設當初也許有種種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有一條,它對于改變我國整個工業布局,特別是支援大西部、西南的建設,起了一些積極的作用。并且經過調整改造,現在有相當一部分三線企業形成的生產能力是非常大的。
比如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重慶船舶工業公司,我去搞承包制的時候,印象最深。當初,很多人認為它是包袱。也難怪人們會這么想,那時整個產值只有8000萬,現在已經是幾百個億的產值了。當初之所以產值這么低,第一,因為那會兒剛把生產線打通,沒有投產,生產力還沒有開發出來;第二,工廠所處位置實在是不合理,太分散了。經過調整,一部分工廠遷建;留下來的,像萬縣個別工廠在三峽工程建起來以后,都淹到水里面去了,實在不行,就想辦法往上搬,在搬遷的過程中,生產結構也得到了一定的調整。這一片廠后來在利川形成的生產能力比較穩定,涵蓋了機械、風力發電以及電子設備生產等生產領域。某個搞柴油機的加工廠,早期還沒有形成生產能力,后來就到鐵路系統去找合作,最后干脆專門搞車輛總裝,為鐵路機車、貨車制造車輛和配套件。那個廠只用了幾年工夫就很快地改造成功,變成了骨干廠。后來開發的產品,比鐵路系統搞的都好。分散在云南的三線企業,則被集中到了一起,形成了一大片魚雷廠。
三線建設也為船舶工業輸送了大量人才。我們培養起來的三線干部,后來也有在總公司當家的。像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現任黨組書記、總經理李長印,他大學畢業后,就到三線去搞江云機械廠。他從跑地皮開始做起,對三線建設的體會是最深的。我在抓三線建設調整改造工作的時候,他就在那個廠當廠長,當時他只有34歲。重慶船舶工業公司成立之后,李長印歷任副總經理、總經理,后來調到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工作,而后總公司一分為二,分成中國船舶重工和中國船舶工業兩個集團,他成為了重工的總經理。
還有一位是國防科工委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現任中國船舶工業行業協會會長張廣欽,他曾擔任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副總經理,很有經驗,也為三線建設出過不少力。
前些年,我到四川一家三線企業去看一位1938年參加革命的離休老干部時,我問他有什么要求,他拉著我的手說:“搞好工廠,就是最大的心愿啊!”望著他那蒼蒼白發,聽著他內心的呼喚,這位老同志憂廠憂國、獻身三線事業的拳拳赤子心,又一次深深感動了我。
現在,有的三線企業已經調整搬遷到了大中城市,但它們畢竟處于軍轉民、再創業時期,困難很多,難度很大。我相信,曾經創造出三線建設輝煌的三線人,曾經在荒山野嶺中開辟出道路的三線建設者,也一定能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再造輝煌。
搞民品還是得“走出去”
我國的船舶工業從一開始起步就是以軍為主的,軍、民品一度由六機部和交通部分開管理:六機部負責為海軍造船,雖說搞一部分民船,但是仍以軍為主;交通部的航運部門則是搞民船的,但卻以修船為主,我們的民船連萬噸輪都很少造。60年代末,沿海的運輸船太少,甚至沒有船可以開展遠洋運輸。因此,民品的發展被提到了議程上來。70年代末80年代初,交通部專門提出500萬噸位的規劃,規定其中要搞多少民品。這個時候民品才開始有新的發展。
與其他幾個機械工業部相比,六機部是一個小部,原來是從一機部分出來的,民品的市場沒有打開,很少有人訂貨。正在一籌莫展之際,鄧小平同志在聽取國防工業匯報后作出了重要指示:船舶工業要想辦法搞出口、找出路。那時候我從東北調到了六機部工作,所以開始研究如何打開民品的國際市場。我們想了很多辦法,發現最后還是得自力更生、以我為主。我們搞了一個技貿結合,通過跟國外搞一些貿易,來引進技術、進行交流,并且要消化吸收。打開窗戶以后,我們看到,外面的世界很熱鬧,光封閉著不行,沒有前途。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國務院直接抓經濟體制改革。國務院和中央領導通過對工業部門進行盤點,又考慮到船舶工業本身的性質,所以準備把六機部的造船部門和交通部一個專門管造船、修船的工業局合并起來,成立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并將其定為第一個由工業直屬部門轉變為經濟實體的試點單位。1980年冬,成立了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籌備小組,我是成員之一。后經國務院批準,總公司在1982年正式成立了,我擔任副總經理,當時正好50歲。從此,產業結構正式由原來六機部“以軍為主”的方針轉變為“軍民結合、軍品優先”的方針。
 中國首艘按國際標準建造的出口船舶“長城號”,它是改革開放后按國際標準建造的首艘大型出口船舶,開創中國船舶出口新紀元
中國首艘按國際標準建造的出口船舶“長城號”,它是改革開放后按國際標準建造的首艘大型出口船舶,開創中國船舶出口新紀元
到了1997年,我們不僅有了一條30萬噸的民船生產線,而且通過“長城”號(這是國家為了通過香港來打開出口船市場而生產的2.7萬噸貨輪首制船)等出口船的建造,為進入國際市場開創了新局面。“十五”規劃以后,我國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這下子船舶工業的生產規模就都上來了。并且,隨著電子技術的發展,生產周期大大縮短,無論是船型還是生產環節,都得到了優化。這樣,我國整個船舶工業的發展都不能以跨越式來形容了,而應當說是飛躍式的。現在我們的船舶工業已經位于世界先進行列,從90年代我國船舶工業打開國際市場大門開始,現在大概有上百個國家都有我們的產品。
由大走向強
船舶工業是很重要的。船舶是漂泊在水上的建筑物,陸地上的建筑物有的,它都有。因此,船舶制造把鋼鐵、機械、通信、電子等產業整個都配套了起來。此外,我國的海洋開發技術,包括水動力等研究,也都在造船工業部門里。建設海洋強國,船舶工業給予的支持力度也很大。
過去,我們很希望能把船舶工業這個蛋糕做大,目前看來是做到了。如今,我國的造船能力早已今非昔比。現在的技術更加扎實,而且比我早期所預想的生產規模大很多,光從產量上講,民船的噸位是第一的。過去,假如我們的船舶工業年產值達到100億人民幣,就高興得不得了了,現在都已經是4500多個億的產值了。但也不能因此而輕易地講這是造船能力過剩,我們不能這么簡單地看待我國船舶工業的發展。
我擔任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總經理期間,曾到世界各個造船國家去參觀訪問,發現我們的做法是對的,生產規模確實該擴大。但是完全一敞開,就有一個問題,各地一看造船有利了,積極性特別高。跨世紀以后的發展規模,是我們誰都沒想到的。2003年我們還在琢磨怎么能夠讓船舶工業在原有基礎上實現“十五”計劃,等到地方上撒開了以后,江蘇、浙江、山東,還有后來跟上的福建,沿海的造船公司跟雨后春筍一樣地起來了。當時我說,你們要有一個思想準備。因為從目前看來,造船行業一直走的是一個波浪形的路。造船行業這一路走來,受到了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并不總是一路向上發展的,因此得按規矩來,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搞商品經濟,如果市場有什么變化,我們把規模搞得太大,恐怕將來要吃苦頭的,韓國、日本都有這樣的例子。到了2005年的時候,船舶工業經濟建設的安全問題就出現了。《國家安全雜志》主編約我寫文章,我寫道,我們的造船增產速度可能是要回落的。到了2007年,新的金融危機初現端倪,造船增產速度卻還在往上沖。大家都很奇怪,紛紛對我說:你說的不對呀。我說,你看著,還沒到時候。
這是因為,造船的經濟環境比較滯后。跟一般的商品生產不同,造船的特點是生產周期比較長,在人家不景氣的時候,我們反而可能很景氣。現在的船舶工業,特別是中船重工,雖然產能很大,但仍有很大的盈利,也在穩定發展,因此也還在繼續往下做。同時,造船的經濟環境也是可以超前的。這是因為造船是以銷定產的。我們過去是每年到年終的時候發通知,把各要船單位召集到一起,然后再擬訂出計劃下發給各廠;現在則是各單位自行訂貨、要船。貨品多了,航運情況比較好,我們的訂單自然就多。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根據經濟形勢進行預判,主動地控制、調整造船產量。因此,在當時,我就建議不要過多地搞造船廠,最多可以搞一個修船廠,至少船總是要修的。但是修船廠搞這么大是不是合算,也要去衡量。
過去,我們的船舶工業從無到有、由小變大,為全面建設打下了基礎。現在是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我們船舶工業也應當在戰略上作一個新的轉變,就是要由大走向強,能夠讓占我國1/3的海洋領土發揮作用,讓中華民族站得更高、看得更遠。而我們造船人的使命之一,就是要為國防、為部隊提供優良的裝備,御敵于國門之外,如果有敵來犯,我們就把他消滅掉。現在,我們的海軍可以在海上駕駛自己的軍艦進行巡邏、防御海盜,我為我們的船舶工業在國防事業中所作的貢獻而感到自豪。
現在的船舶工業是比以前困難了,但困難的性質不一樣的。這是一個由大到強的轉變,比起過去,可能是在思想意識上面更困難一些。就像富裕的人過慣了闊日子,過緊日子不習慣。我們以前要能夠抓著一條船的訂單就高興得不得了,現在抓著一條船、兩條船還不太過癮,喂不飽呀!我們要在此基礎上,認真研究怎么進一步實現由大到強。
其中,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加強行業協會的作用,起碼是行業協會的建設。中國船舶工業行業協會是1994年我當總經理的時候籌建的。當時考慮的是,既然有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我們就應該有一個船舶工業的行業協會來搞信息服務,對完成任務情況和市場的動態進行實時發布。經國務院批準,協會于1995年4月成立。多年來,協會發揮了橋梁和紐帶作用,為政府、為企業服務,很好地促進了我國船舶工業的發展。
目前,這個協會就在原來六機部辦公的大院里。我40年都沒有離開這個地方,所以對這個院子很有感情。有時候,我在這個院子里會感慨萬分,偶爾也會回顧一下過去的人生。我們每個人的終點在哪里,其實從一開始就都是知道的。什么時候通知我,我就去,不通知就不去。但是話說回來,活著真好,活著可以看到很多事情,很多那個時候我們根本沒想到的事情。
來源: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