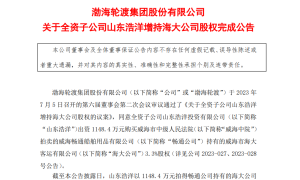認定有“顛覆性的轉變”并不意味著已經知道“顛覆后”航運業會是什么樣子,而是仍然在摸索之中。總之,航運業充滿了不確定性。
“十二五”期的五年對于航運業來說,用“激蕩”來形容不為過。我覺得可以用兩個詞來概括航運業的境遇,第一個詞是“轉變”,整個行業處在顛覆性的轉變之際;第二個詞是“摸索”,認定有“顛覆性的轉變”并不意味著已經知道“顛覆后”航運業會是什么樣子,而是仍然在摸索之中。總之,航運業充滿了不確定性。
以往的觀點認為,貿易的起落實際是貿易量在不同區域間的結構性重組,世界貿易干線在不同區域之間發生轉移。而現在的狀況是,產業鏈的上下游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區域貿易、雙邊貿易、本地生產等的新形式層出不窮,技術本身也在發生代際轉變。加上以大數據應用為核心的市場資源重組,已經從根本上重塑了消費形態、生產形態,作為消費與生產的連接服務之一的航運業無疑也在被重塑中。
雖然航運業的歷史性轉變充滿了不確定性,但并非除了等待就無可作為了。航運業的發展歷史絕對是一個“試錯”的歷史,航線的設計、船型的開發、貿易的轉化無不是在無數次失敗的嘗試之后慢慢形成固定模式的。而從根本上來說,基于集裝箱運輸的國際貿易與千年前“海上絲綢之路”木質多桅帆船承擔的東西方貿易,并沒有區別,它們的差異可以認為是“量”與“式”的差別。基于此,我以為,現在我們面臨的是要打破圍繞船舶運輸形成的航運業的主體性,而讓船舶運輸成為平臺交易的“一個單位”,成為從產地到加工地再到終端的整個產品生命歷程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觀點來自于對于“平臺”和“大數據”兩大當代經濟靈魂的認知。
在摸索下一步航運業的形態過程中,過去的五年無疑是關鍵的“試錯期”,我得出4個關鍵詞作為其表征。
第一,運價
航運市場的一切變化都是圍繞著運價展開的,生意嘛,做來做去就是從價格開始的。運價絕對當得起這五年的第一主題詞。
2010年,海運市場最熱門的話題當屬運價。2月2日
BDI報收651點,當時已是歷史新低。但是,五年之后的今天BDI又創出了歷史新低,終于跌破“5”開頭時代低至471點(1月7日,BDI指數收于445點,較前一天下跌4.71%,再創歷史新低–編者)。與此同時,五年來上海出口集裝箱運價指數(SCFI)也從2010年年中的1500多點跌到去年12月最低的484點。
這樣的形勢下,市場需要一面鏡子,能看得更加清楚、更加明白。而在一開始,我就在琢磨如何做這面“鏡子”.很顯然,指數是反映這個市場的最好的“鏡子”.幾年來,上海航運交易所一直在對指數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從集裝箱領域到散貨、再到買賣船領域;從出口到進口,再到區域市場;從最開始的發布指數點數,到直接公布運價;從表征總體市場到專注更為靈敏的即期市場;從每周發布到每日發布。每一步改革,都是為了讓鏡子更加明亮。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指數,并把指數真真切切地當作一種工具。
去年9月,我拜訪英國《勞氏日報》集團。會談時,《勞氏日報》總編尖銳地問我,如何看待有航運企業的抱怨–SCFI讓行業狀況進一步惡化,因為SCFI提供了完全透明的、反映現貨市場運價的信息,加劇市場的波動。我當時的回答是:運價是由市場決定的,SCFI只是真實反映運價波動,而不是加劇波動,信息透明才是成熟市場的標志。《勞氏日報》當天發表了題為《上海航運交易所總裁堅決捍衛SCFI》的報道。我說:對于SCFI,與其避之,不如用之,船東的態度應從如何控制市場向如何應對市場轉變,而指數將是應對市場不可或缺的工具。
運價下行趨勢已經提醒我們:無法用傳統的成本概念來衡量航運業的財務核算狀況。隨著運價一再下降,對于成本的考究也在深入,從根本上帶動了航運業走向變革的深水區,也就是低運價時代航運的獲利能力。
為航運業托底的傳統指標已被一再突破,航運業在受到挫折的同時,沒有顯露出停頓的跡象,也沒有因為極低的運價而崩盤。引起我思考的是:航運業的現狀已經不能用傳統思維方式來等閑視之,它其實已經在適應新常態過程中向前邁出了寶貴的一步。新的市場價格的平衡點已經不是過往的那個水平,我們已經回不去了。外表的價格下行表明內部的結構已經被重寫。這說明行業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時期,這個時期會改變傳統航運的模式。
第二,大船
五年來航運業值得一書的事件之一就是“大船”的出現,無論是散貨船(船型 船廠 買賣)還是集裝箱船(船型 船廠 買賣)都不斷“長大”.
2011年2月,馬士基集團斥資約19億美元訂造10艘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載箱18000TEU的集裝箱船,一年后該批船開始陸續投放市場。而現在,集裝箱船已經造到21000TEU.可是,最新的消息表明,最早的一批大船已有被閑置的了。散貨船則有淡水河谷的40萬噸級礦砂船(船型 船廠 買賣)作為代表,紛紛擾擾爭吵了幾年,最后還是被接受在中國海港停靠。可是此時旺盛的礦砂需求卻煙消云散,運價在持續下跌,離五年前人們經常說的1500點BDI運營平衡點越來越遠。
一般認為如果一家企業沒有能力前瞻業態轉變前景,就不可能長久立于不敗之地。誰先掌握行業前景,誰就能在一定時期內掌控行業走向并從中受益。當時我曾預言,今后五年大船訂單會不斷地重復出現。而當時大多數人還在糾結大船的可行性,還在以運力過剩為借口質疑大船的“合法性”.
我一直認為,市場的運力過剩不代表企業運力過剩,企業如果出現運力過剩只能說明一點:自己的市場競爭力喪失了。運能過剩,本質上講就是這些造大船、造先進船的企業進行行業競爭的“武器”,“過剩”必然產生擠出效應,技術落后、單位成本較高的航運企業會被淘汰,無論它原來多大,這就是自然生存法則。競爭是“永恒”的主題。當競爭可能造成兩敗俱傷,航運企業會取妥協姿態,通過減少摩擦求生存,但是,一旦出現打敗對手的機會,你死我活的競爭又走到前臺。一塊地盤上不可能同時生存兩個獅群,有人夢想的航運企業間和平共生的“烏托邦”不存在,對行業競爭的“浪漫主義”的觀點,是一種有害的從業心理。
也許有人看到的“大船”,是一種“量”變,我倒是更多地注重“時代”的特質。作為“時代”,在一個時間段將有它自己穩定的特征和個性,“大船時代”的特征就是運營的低成本和資產的高效率,它對應的時代特征就是對成本和效率管理的精細化。當大船的市場穩固了,可能就不需要這么多的航運企業了。這話出自強者之口就是一種警告,出自弱者之口就是恐懼。
但是,現在看來大船可能也不是“終極”形式。馬士基灣水大船或許就是苗頭之一。那么,航運業“終極”的方向在哪里呢?需再摸索。就像馬士基將行業領入大船領域一樣,還會有企業會將大船領入新時代。這個時代是什么樣我說不清,但一定是與大數據充分利用和快速處理有關。合理的配送體系目標是將成本降到接近于零,船舶運輸要如傳送帶和流水線一樣精確和快速,自成體系的海運(特別是集裝箱運輸)會“解構”成為“快遞的一環”.
第三,聯盟
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航運業在調整運力的同時,展開了廣泛的結盟運動。我曾經指出過,事實上,聯盟已經成為航運企業保住市場份額、擠壓競爭對手、控制利潤規模的重要手段。所以,人們對它愛恨交加,情感復雜。原因有三:第一,參與聯盟的企業獲得了市場份額、價格和艙位資源的保證,對于它們,聯盟就是一道“護身符”;第二,沒有參與聯盟的企業,市場份額被蠶食、價格體系崩潰、單打獨斗艙位資源匱乏,對于它們,聯盟就是一道“奪命符”;第三,托運人因為聯盟降低市場競爭激烈程度而不再有機會獲得更低的價格和更多的服務選擇,對于它們,聯盟就是一道“緊身符”.
但是,聯盟在很多國家很多層面受到嚴格控制。FMC前主席李丁斯基到訪上海航運交易所時曾經形象地說過:我們要共同看住這些“大家伙”.
我在一篇發表的文章中曾經指出:企業聯盟并不一定是市場的“反動力量”,在產業發展的很多階段,聯盟企業無疑是產業創新、進步、成長的核心力量,它能夠更集中和有效地提供市場所急需的先進技術、高速效率、適度規模、穩定價格、多樣服務,這些都是分散的市場所無法有效提供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講,聯盟的出現是市場作用的結果,沒有它們,市場就會失去發展動力。同時,市場也會尋找新的動力去打破這一聯盟。生物體的生長規律是通過不斷結構與解構,達到新陳代謝、吐故納新。很難評價聯盟的優劣,各方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很難獲得一致看法。有一點人們必須相信,市場未必如人們想象的那樣脆弱,市場會調整其神經“大條”來應對包括聯盟在內的各種變化。
從歷史看,現在是海上商業力量最多元化的時代,人們可以反對商業壟斷組織,但不能反對商業上的降本增效,反對也是徒勞,商業就是要實現“成本和效率”的再優化。因此在現行產業環境背景下,航運企業有了改變自己整體競爭態勢的基本沖動。這樣看來,寡頭的形成反而有利于弱者聯合,而弱者聯合是防止寡頭快速成長為壟斷者的主要力量。防止壟斷的出現,并不天然具備“道德”上的正確性,產業政策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確保產業順利實現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
聯盟有未來嗎?我的觀點是,如果說大船的未來還有一些令人疑惑的地方,那么聯盟則是肯定沒有未來的。因為,航運業特別是集裝箱的發展力量來自公共平臺對于傳統組織(包括聯盟甚至企業)的“解構”,船舶運輸基于有效的公共平臺會向著無差別的單位化運能轉變。一旦一定數量的運能在平臺上成為抽象的“單位運力”,聯盟和企業將不再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了。
第四,衍生品
2011年6月28日,中國航運運價衍生品交易在上海開市,航運運價衍生品的誕生對于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建設具有標志性的意義。因為這是全球首個航運運價第三方集中交易平臺,這對中國在國際航運領域爭取話語權與定價權具有重要的作用,國際航運界出口集裝箱中遠期運價首次亮出“中國價格”.
對于置身航運產業鏈中的貨主、航運企業、船東、貿易商、金融機構等,一個穩定的、能夠持續健康發展的市場是至關重要的。現在市場有了這樣一個平臺(產品),這是業界共有、共享的公共服務項目。我以為,只要市場有需求,相關的產品就一定會應運而生,我們不做,別人會做;中國不做,外國會做。事實上,英國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有運價衍生品。上海航運交易所2009年發布新版中國出口集裝箱運價指數,僅3個月就被英國的經紀公司開發成衍生品。所以,我們必須有自己的衍生品。
當時我們選擇運價衍生品現行方式的目的主要是應對運價問題。長久以來,運價波動已經到了讓承運人和托運人均難以承受的境地。以歐洲航線運價為例,那時,一只標準箱運價在500~1700美元之間變化,20000TEU型船,每個航次就有2400萬美元損益,八九個航次下來,船東要么賺進一艘船,要么損失一艘船,用“瘋狂”兩字也不足以表達其劇烈程度。而以上海港一個港口出運到歐洲的運量來看,保守估計350萬TEU重箱運量,運價風險敞口高達40億美元。而中國煤炭海運市場運價同樣也有著3倍的波動。
市場風險畢竟是天然的存在,光靠避閃是非常被動的,我們想通過設計一種工具管控運價波動引起的風險,運價遠期交易就是其中之一。但是,運價指數遠期交易不是“諾亞方舟”,更不是“救世主”,它本身也有風險,但這不足以抹殺它的效力。
在我慢慢形成航運業終將借助平臺成為單位化的運能的觀點后,運價衍生品也因此超越了工具的作用,具有了本體的性質。當運能成為平臺交易單位時,運價衍生品必然成為其不可或缺的交易組成部分。通過對沖實現的運輸環節的價格風險將成為與買保險一樣簡便的事情。從交易途徑看,很可能只是在運能單位交易結算頁面點一下衍生品的按鈕,簡單選擇即可下單。并且在平臺上,它不再是行業大佬們或者投機博弈者的專利,而是普通運力單位購買者的“制式”購買行為。簡單如淘寶運價保險一般。
不可否認,由于市場發育的不成熟,同時由于產品設計的缺陷,現在的運價衍生品交易遠沒有達到正常的交易程度。但是,隨著航運業發生顛覆性轉變,運價衍生品會作為“顛覆性”的必需品受追捧。
路徑可以修正,并且必然不斷地修正,目標是堅定的。
讀者可能已經發現,無論是運價、大船、聯盟還是衍生品,歸根到底我是在說“成本”.同時,成本的結構在發生變化,傳統行業中的成本與新型行業的成本,不僅構成不同,而且通過平臺和衍生品等新型工具,本質也在發生變化,這也是當前時髦的“供給側改革”在航運業的雛形。在大數據和公共平臺的環境下,傳統意義上的成本甚至會消解–出現零成本。航運業現在還想象不出“零成本”,但是長時間的低成本運行,或許已經暗示我們:航運業的成本線已經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一切都在變,一切皆有可能。
我曾經撰文指出:應變和制變的能力是主導力量的核心競爭力。中國企業應該更深入地認識市場化的力量,并由此認識和建立市場主導能力。這種能力不是奢望將市場拉回到若干年前那種“好日子”的能力;這種能力是促進航運業轉變的具有預見性的推動能力;這種能力是推動企業轉變以往模式、主動進行供給側改革的勇氣。
這五年對航運業可謂嚴冬,但窮則思變,五年的航運業在思變中度過,如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寒門出才子一般,篳路藍縷,勇猛精進。最后我還想說,航運除了是一種生存方式,還是一種生活方式,我們除了追求利潤之外,還應該追求一種情懷!與水相融,與海為伴,那才是人生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