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冠肺炎疫情的加劇讓醫院船頻現中外新聞。配備有1000張標準床位及12間手術室的“仁慈”(USNS Mercy)號以及規模相當的“安慰”(USNS Comfort)號先后支援洛杉磯、紐約。這兩艘海軍醫院船在當代美國應急響應、醫療外交的重大行動中功勛卓著,曾參與9·11事件傷員救治、拉丁美洲醫療援助以及2010年海地大地震后的衛生保障工作。不過在八十年代后期才由運輸貨輪改裝而來的“仁慈”號、“安慰”號著實只是西方世界海軍醫院船的“初生牛犢”。從1850年代世界首艘規范化海軍醫院船“墨爾本”(Melbourne)號在英國投用并受派駛往中國參加第二次鴉片戰爭起,海軍醫院船已伴隨人類軍事史、醫療史走過了一又四分之三個世紀。期間,兩次席卷全球的世界大戰成為了海軍醫院船履職的重要舞臺,而真刀真槍的戰爭語境又讓各國海軍醫院船在建設、醫療服務乃至國際公約保護等方面向前跨出了重要一步。以下我們將溯流而上,重溫兩次世界大戰中英美海軍醫院船的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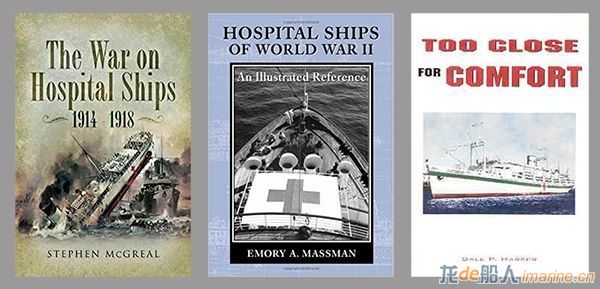
兩次世界大戰醫院船研究代表作書影
“變身記”:兩次世界大戰中英美醫院船的由來
英國的“墨爾本”號開近代世界醫院船之先河,而大洋彼岸的美國也緊隨其后創造出了首艘美軍醫院船,軍醫史學界公認美國歷史上最早的醫院船是南北戰爭期間的側輪汽船“紅色漫游者”(Red Rover)號。此后半個世紀間,英、美兩國均打造了若干醫院船配備給海軍并陸續更新換代船載醫療、后勤設備。至20世紀初,英美兩國都已具備成熟的醫院船裝備能力并習慣了有軍醫船隨航的戰時保障模式。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狼煙四起,正對歐洲大陸的海洋霸主英國迅速投身戰局。為支持英國贏得歐戰,各自治領紛紛向英國本土運送補充兵員。一些容積闊大的商船被征用作運兵船,部分運兵船又再次被改裝為醫院船。譬如舷號HMATA63的澳大利亞首艘醫院船“卡羅拉”(Karoola)號,它原本是墨爾本航運企業麥卡恩公司(McEeacharn’s Line Pty Ltd.)旗下的一艘大型商船。1915年6月,“卡羅拉”號被征召擔負由澳大利亞運兵埃及的任務。在航抵南安普頓時,“卡羅拉”號被英國官方截留,旋即改造為一艘擁有288張床位、可同時容納460人就診的醫院船。一戰期間,英國軍方改建了多艘與“卡羅拉”號情況相似的商船,為改造醫院船而征用的商業海輪普遍具有大噸位特征,基本集中在1200至1800噸的區間。對造船工業產能、船舶制造原料都頗為有限的戰時英國而言,借助體量龐大的現成商船來改裝醫院船確實最為經濟、快捷、穩妥。
但對于向醫院船改造項目捐獻船舶的航運企業而言,財產“一去不復返”并非危言聳聽。一戰期間,20世紀英國著名航運企業聯合城堡公司(The Union-Castle Line)將大部分所屬船只貢獻給英國政府。不幸的是,該公司所捐“蘭多維利堡”(Llandovery Castle)號等8艘艦船在遭德軍艦艇水雷或U型潛艇攻擊后因受損過重而最終沉沒。

一戰期間從郵輪改裝為醫院船的“瑪希諾”(Maheno)號
1917年美國拋棄中立政策,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戰。與英國重點改裝商船的醫院船生產思路不同,一戰美軍醫院船基本來源于翻修海軍現(退)役艦艇。1918年1月24日,由一艘1907年下水軍艦改建而成的“仁慈”(Mercy)號醫院船入編服役。1918年11月3日,“仁慈”號首次前往歐洲戰場,此后五個月間它四次往返于法國與美國之間,運回了大批負傷美軍士兵(僅1919年3月的末班航程該船就接回了多達1977名傷亡軍士)。“仁慈”號等醫院船在一戰期間美國有限的實質性軍事行動中積極馳援,救死扶傷效果卓著,于海軍內外廣獲贊譽。
在經歷“二十年的休戰”后,第二次世界大戰如福煦之“約”血色降臨。1939至1940年間,英國醫院船在歐洲戰場海軍行動以及配合西歐地區陸上作戰方面有所作為,但也因德軍強悍的追擊付出了慘重代價。在英軍醫院船陷入僵持狀態后,二戰期間美軍醫院船卻因太平洋戰爭爆發獲得了一展身手的契機——太平洋諸島攻堅戰中均出現了醫院船身影。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加速擴張海軍力量,在造航母、造潛艇的同時,醫院船也被提上了議程。由于時間倉促且美國戰略物資奇缺,一戰期間美軍改裝舊艦艇為醫院船的策略得以延續。二戰期間美軍在役年數最久的醫院船是下水于1920年的“撒馬利亞”(Samaritan)號,該船本為長途貨運用船,在1944年被臨時改裝成醫院船。同樣情況還有1943年蛻變為醫院船的“慷慨”(Bountiful)號,前身是同年退役的美國海軍“亨德森”(Henderson)號運輸艦。由于運兵(貨)船本身結構適宜,醫院船改造項目往往只需安裝一定醫療設備(手術間)以及依照國際法慣例重新包裝。1943年美軍“救濟”(Relief)號醫院船入廠改裝,由通體銀灰色改漆為白色并加涂巨大紅十字標志,并以綠色飾帶環繞全船一周。由于僅是外觀調整,“救濟”號得以快速下水投入太平洋前線救護工作。據統計,1941至1945年,美軍共改裝27艘醫院船,其中24艘由戰爭部調配,3艘由海軍部直轄。此外二戰期間還有12艘美國海軍艦船也曾臨時充任轉運前線傷員的軍醫船角色。

二戰期間美軍3艘“安慰”級醫院船之一的“希望”(Hope)號
“醫船不醫”:兩次世界大戰中英美醫院船的服務
不同于現代醫院船海外醫療援助新聞呈現給公眾的視效,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軍隊醫院船的本職是從前線、野戰醫院向大后方醫院(甚至本土)轉送傷員,并沒有適當設備或人員來直接處理成千上萬的戰斗傷亡者。一戰期間英軍戰略規劃明確醫院船的第一使命是將傷病員運送回英國本土接受進一步治療。我們并不否認醫療船有救治功能,但船上有限的醫療資源多是針對乘客傷員的急診救治(包扎止血、創面初步清理等),諸多后續治療將留待目的地軍醫院繼續開展。
英國醫院船在轉運傷員方面表現出色,形成了長途與短途兼有的醫院船航線組合。長途航線將歐洲戰場傷病員護送至各自治領深入救治。譬如1916至1918年“卡羅拉”號行駛在澳大利亞與英國之間,去程運送陸軍醫療隊、澳大利亞醫院運輸隊等醫護援軍奔赴英國,返程則護送大量傷病員返回澳大利亞休養。短途航線上的醫療船基本往返于英國本土與法國戰場之間。“列日”(Ville de Liege)號便是此類短途醫院船的杰出代表。1917年6月至1918年12月間,“列日”號醫院船共計出航252次,在英國本土與歐洲大陸(法國)之間運送了77194名傷員以及替換補充的36356名上陣士兵,立下不朽功勛。

二戰期間美軍太平洋艦隊司令部的救護車前往醫院船轉運傷員
與一戰英軍醫院船的處境如出一轍,二戰期間醫療船對應美軍軍醫體制中的“第三級醫療”(Echelon III Medical Treatment),這也是戰地軍醫服務的最高層級。醫院船在此分級診療系統中主要負責為第一級(戰地救護)與第二級(據點野戰醫院)提供醫療支持、在危難時轉運前兩級治療單元病患,以及為需要住院的病號提供留觀條件。二戰期間的美軍醫療船雖裝配了不少具備急救條件的手術間,但失血較多、感染風險較高的手術操作依舊難以在船上完成,對于現代大型外科手術至關重要的血庫、生命體征監控設備均遲至朝鮮戰爭方才裝配上醫院船。總體而言,兩次世界大戰間醫院船“醫而不醫”的國際性特征并未消解,轉運傷員依舊是所有醫院船活動的核心要義。

一戰英軍“加斯科涅”(Gascon)號醫院船正在轉運擔架抬送來的傷員
“不武裝”悖論:兩次世界大戰中頻遭攻擊的醫院船
1907年《日內瓦公約原則適用于海戰的公約》(《海牙第十公約》)規定醫院船是“各國特別并專為救助傷者、病者和遇難者而建造的裝備或船只”。《海牙第十公約》對簽約國的醫院船有兩點明確要求:第一,交戰國軍隊應將下達給醫院船的全部命令造冊入航行簿以備隨時查勘;其二,醫院船應當進行明顯的噴涂、掛旗標識,具體包括漆白船身、添加醒目的紅條標志及與本國國旗并列懸掛《日內瓦公約》確定的白底紅十字旗。

St. David號遺存的老照片清晰顯示了船體側面的紅帶、紅十字標示
《海牙第十公約》事無巨細地規范交戰國醫院船標識,其根本目的是利用國際法約束力保護各國醫院船在戰時免遭攻擊,任何在軍事行動中攻擊醫院船的行為都將被海牙公約框架視同戰爭罪行。為避免出現參戰國假借醫院船“暗度陳倉”,《海牙第十公約》也配套地明令禁止醫院船裝載任何武器,交戰國有權登臨醫院船檢查武裝情況。
但殘酷戰爭并不能為國際法理的簡單正義規訓。如此,“不武裝”悖論便橫亙于醫院船面前。若保持“零武器”狀態,實戰中醫院船往往會被敵國海、空軍緊盯作首要目標,在毫無反制能力的前提下被各種借口裝點的武力措施擊沉;若添設武裝,則國際公約認可交戰國對醫院船實施攻擊行動,人道主義救援將徹底喪失最后的法則庇護。
對敵國醫院船這個防御薄弱環節窮追猛打的戰略在德國海軍中廣受歡迎,某些德軍潛艇指揮官將之奉為圭臬。一戰期間德軍潛艇精英瓦爾特·施威格(Walther Schweiger)上尉就曾率領部隊連續擊沉“盧西塔尼亞”(Lusitania)號、“阿斯圖里亞斯”(Asturias)號兩艘醫院船,使協約國陣營蒙受不小損失。

遭受敵軍攻擊而破損進水的“格洛斯特堡”(Gloucester Castle)號醫院船
一戰中德軍打擊協約國醫院船制造了諸多慘絕人寰的悲劇。1918年8月3日,澳大利亞醫院船“瑪蒂爾達”(Warilda)號被德國潛艇UC-49發出的魚雷命中,因機艙嚴重進水受損而沉入海底。位于“瑪蒂爾達”號底部、安置輕傷(可以自由行走)患者的“I區”全艙101人無一幸免。這些士兵本是輕傷卻因飛來橫禍而殞命深海,實在令人唏噓。
據軍事史學家統計,1939至1945年間世界范圍內共有23艘醫院船因戰爭失事。其中英國損失最大,多達5艘,希臘與意大利次之,折損4艘。日本有3艘被擊沉,德國2艘,而蘇聯、澳大利亞、挪威各1艘。此外還有2艘同時擁有荷蘭/日本、意大利/英國船籍的醫院船在戰時被摧毀。從上述23艘醫院船的沉沒時間分布來看,1941年為峰值,有7艘覆沒,其次分別是1943年(5艘)、1945年(4艘)、1940年(3艘)、1942與1944各有2艘醫院船被敵軍毀滅。自摧毀上述23艘艦艇的武器類型來看,幾乎所有醫院船致命傷的直接來源都是飛機投擲、潛艇發射的魚雷。而二戰期間敵對國向醫院船發起的進攻也明顯更為直白、兇殘,除一戰中業已出現的魚雷、水雷游擊、伏擊外,光天化日下的轟炸也摧殘著無法設防的醫院船。“紐芬蘭”(Newfoundland)號醫院船被德國戰機炸穿甲板,船面上正在搶救傷患的6名護士以及附近所有隨船軍醫悉數喪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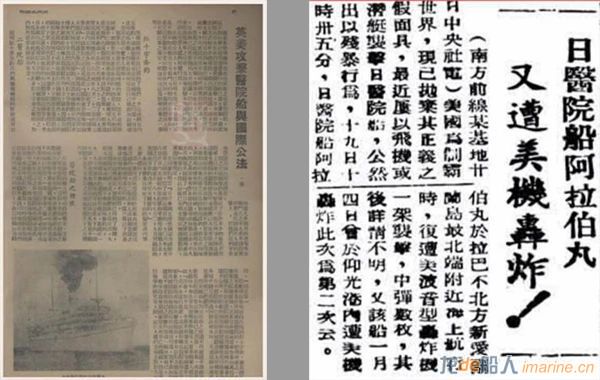
1943年中國日偽媒體以英美轟炸醫院船為題大行戰爭粉飾
值得一提的是,醫院船擊沉事件在二戰期間廣為交戰雙方利用,時常被當作戰爭宣傳資源。經過軍方喉舌的精心包裝,醫院船沉沒事件升格為國際政治要聞,以此為說辭大加討伐敵對國(陣營)的案例屢見不鮮。譬如1943年美軍擊沉日本醫院船后中國的日偽媒體借機刊出長篇大論痛批“美國暴虐”,鼓動“東亞人民”仇視美國。不過事實上,日軍在二戰期間也曾多次攻擊美國等反法西斯同盟國家的醫院船,并有擊沉前例。
八年前羅蘭·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執導的科幻片《2012》火遍全球。電影中四艘諾亞方舟承載起了人類扛過毀滅性生態打擊的全部希望。作為一則出自《舊約·創世紀》的基督宗教傳說,“諾亞方舟”在后世被頻繁演繹為災難敘事的表征。同樣,“船”的救世意象在佛教中也廣為流傳,所謂“慈航普渡”、“寶筏”便是典型符號。烽火狼煙、遍地尸骸的兩次世界大戰中,醫院船穿行大洋,盡最大努力將流血掛彩的將士們帶離魔鬼前線,將生的希望散播在肅殺焦土之上。我們怎能不將兩次世界大戰中的醫院船與宗教拯救傳說中的那些“船”聯系在一起呢?在美軍歷史上,曾有過三艘代代相傳的“仁慈”號醫院船:AH 4(1918年)、AH8(1943年)、T-AH 19 (1985年),或許三艘艦艇舷號變換所映襯的船名庚續,恰好暗示了醫院船的本質——知危不退、守正行善。即便無法拯救全部,也要在殺氣騰騰的非理性時空中最大程度保留仁慈的火種。
作者:鄒賾韜(上海大學歷史學系)
來源: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