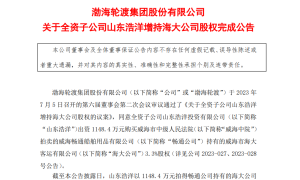1 產業政策是“回歸計劃經濟”還是“權宜之計”
大家想必最近都在關注張維迎和林毅夫就產業政策的爭論。張維迎是市場派的旗手,堅信市場力量,否定政府的作用,其核心論點是市場決定和企業家精神。林毅夫則一直倡導比較優勢和政府有為論,其核心觀點是:過去以價格扭曲和市場壟斷,來保護補貼在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國有企業,是維持經濟社會穩定的必要措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政策;現在,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中國已經是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資本已經不再極端短缺,許多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現在已經符合比較優勢,再給這些產業中的企業保護補貼,對穩定經濟沒有必要,只加劇了尋租、腐敗和收入分配不均,就需要與時俱進地給予改革。轉型中國家最終所要達到的目標是消除存在于經濟中的各種制度扭曲,建立完善的、有效的市場經濟體系。楊小凱和張維迎的框架中認為這些扭曲是政府強加的、外生的,所以去之惟恐不及,越快越好。林毅夫同樣認為這些扭曲是政府強加的,但是,是內生于保護貼違反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的需要的,是在當時條件下所能做出的最優選擇。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從來都是極具爭議的問題,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不同的發展環境以及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對于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都會有所不同。一般來講,經濟蕭條期凱恩斯主義就會大行其道,而經濟復蘇期則是市場自由主義大行其道。而實際上,自從有了現代政府以來,市場和政府從來就是所有經濟主體必須面對的一個綜合體,不存在一個純粹的沒有政府的市場,也不存在一個純粹的沒有市場的政府,二者彼此都離不開對方。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也離不開政府,政府確定稅率、利率、債務、福利以及其他公共產品,政府這只手并沒有消失,只不過相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言,顯得更加“恰如其分”而已。完全沒有政府的市場,是對市場充滿幻想的“烏托邦”,是對“看不見的手”作用的過于良好的盼望。當然,“看得見的手”該如何作用值得探討,是用間接的宏觀調控手段干預經濟好還是直接的微觀產業政策好?通常的認識是政府用好宏觀調控工具,然后構建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但是在部分極端的情況下,宏觀調控手段已然失效,任由部分產業破產引發經濟的連鎖反應恐怕對經濟社會的危害更大。部分對國家長遠發展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也需要國家力量的培育和推動。
2 美國產業政策的案例
賈康在其“產業政策與供給側改革”的演講中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一個案例:美國面臨全球金融危機時“看得見的手”是如何主動作為的。美國人的調控實踐顯然跳出了主流經濟學教科書討論的范圍,在危機發生之后,關鍵的節點上,美國人總結不救雷曼兄弟公司而使金融海嘯迅速升級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的教訓之后,其后相對果斷地先后動用公共資源注資花旗、兩房,并以公共資源注資實體經濟層面的通用汽車公司,成為美國反危機過程的一個拐點,這顯著消解了市場上彌漫的恐慌情緒。美國在復蘇過程中雖然也運用了幾輪量化寬松這樣的需求管理手段,但同時做得有聲有色、可圈可點的是一系列產業政策、技術經濟政策的供給管理措施。比如大家眾所周知的油頁巖革命,不僅是在反危機的過程中提振信心和提升景氣,還實際上對全球的能源格局產生了巨大影響;還有通過制定產業政策促進制造業重回美國。還有一個例子,就是特斯拉在面臨瓶頸期的時候,迎來了美國華裔能源部長朱棣文對特斯拉生產線的視察,跟著很快就有一筆為數可觀的美國能源部的優惠低息貸款,去支持他突破這個瓶頸期。上述例子表明,美國這樣一個視“自由市場”為顛撲不破真理的國家仍然有“看得見之手”直接發揮作用的空間,這就是國家層面的供給管理。
林毅夫也舉了相似的例子。發達國家用稅收和政府采購等來支持新技術、新產品的創新,并用政府資金支持創新企業。以大家津津樂道的喬布斯為例,1976年推出的蘋果I型計算機是建立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美國政府的公共資金支持的計算技術的研發成果上,2001年推出的IPOD和其后的IPHONE也是建立在政府資金支持而研發出來的衛星定位、聲控和大規模儲存等新技術上的,喬布斯的天才在于把這些新技術組合開發成消費者喜愛的新產品。值得一提的是蘋果公司在未上市之前,除了得到風險投資的資金之外,也得到美國小企業局50萬美元的風險股本投資。同樣,Google核心的計算技術也是來自于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1]
對照中國,如果任由市場在任何時候都發揮決定性作用而忽略產業政策的作用,就不會有中國高鐵的世界第一、中國攻克核電第四代技術以及中國大飛機項目的突飛猛進,中國就永遠在發達國家建立的市場規則下處于產業鏈的低端,永無出頭之日。中國國產大飛機C919已經進入取得適航證的階段,如果不出意外幾年之內會配到各個主要航線上,形成前所未有的國產供給能力,而且中國現在已經接到來自全球的幾百架國產大飛機的訂單,以后這個數目還會繼續上升。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的“兩彈一星”是舉全國之力的結果,我國的人造衛星及航空航天領域的大發展也得益于相應的產業政策。9月15日“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在甘肅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成功發射,引發了這樣的思考:國家力量主導的航空航天事業突飛猛進,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發射的成功率為100%。盡管有無數的案例表明國家意志所引發的低效與腐敗,為什么我們的航空航天事業有這樣高的發展速度和成功率?發達國家的市場為什么不能比我們這樣的體系有更好的表現?
賈康還提到,關鍵不是該不該有產業政策,而是構建怎樣的制度讓產業政策能夠真正發揮實效,而不是成為孕育產能過剩和官員腐敗的溫床。“產業政策在創新事項上如何興利抑弊從而實現后發經濟體的追趕和趕超值得深究,必須要考慮供給側管理與改革,以及理性供給管理下如何優化產業政策。換句話說,不能因為政策設計可能失誤,貫徹機制可能走偏,就完全對產業政策、供給管理棄而不用,那是一種無所作為的狀態。應該力求理性,力爭做好,積極謹慎,有所作為。”不能因噎廢食,也不能“孩子洗澡水一起倒掉”。張維迎所說“產業政策就是變相的計劃經濟”這樣的話有一定道理,根本的原因還是我們的制度沒有跟上,無法讓產業政策在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規避可能產生的腐敗、尋租以及騙補等問題。如果相關的制度都逐步完善,那么產業政策將發揮積極作用。同時要認識到,這樣的制度并不是復制西方的制度,而是繼承現有歷史遺產上的逐步改善。這樣的制度只能是中國特色,因為歷史、利益格局、發展階段、發展環境等問題都是個性化的,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永遠正確的制度。和楊小凱共同撰寫《經濟改革和憲政轉軌》一文的杰弗里·薩克斯的思維近些年已經有所改變,其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的成績的評價是:“這在人類經濟歷史上都是很罕見的。”并指出:“國與國之間很難相互比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務,都有自己的困難和挑戰,都要學會解決自己的問題。”
3 水運業中的政府作為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要求的政府應當是“有限有為”的政府。“有限”的含義是:讓市場中遵紀守法的主體感覺不到政府的存在,而一旦違法,政府之手和制度之手就會發揮作用。“有為”指的是在公共服務、國家安全、節能減排和推動戰略新興產業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對于水運業,“有限有為”的政府指的是在水運業的不同領域“看得見的手”應當收放有度,“有所為”但不是“亂作為”,所有過去“越位”、“失位”和“錯位”的應該糾正,而所有“缺位”的部分應該補齊。總結起來就是“松手”、“放手”和“推手”。
松手:讓市場充滿活力。在自貿實驗區探索推行航運業的稅制改革試點;逐步減少政府定價和政府指導價,形成透明的市場價格體系;逐步減少事前審批的事項;探索和規范水運業的費收模式。
放手:構建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與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的綜合部門建立機制;發揮第三方機構的作用;強化港口反壟斷的相關工作。
推手:主動作為。重構水運業的制度體系,讓制度與水運的發展階段相適應;通過公平公正的行業政策解除供給抑制;“海運強國”需要在我國近海構筑海上的支持保障體系,這需要通過國家力量來推動;“海運強國”的人才保障不但需要“航海日”活動的推動,還需要國家拿出足夠的資金來支持,更需要國家在船員所得稅方面形成利好;國際航運中心建設需要中央和地方在營商環境改善方面的主動作為來實現;著力推動互聯網+水運企業的成長,進而推進行業監管變革;在“信用中國”的框架下,推動“信用交通”的行業信用體系建設;培育行業協會、航交所、科研機構以及新型智庫等第三方力量。
從林毅夫和張維迎的爭論中,我們是否能夠對水運國企改革進行反思?在改革開放初期,水運業對國民經濟尤其是對外開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那樣的環境下給航運本不具備比較優勢的國有企業給予產業政策的支持是合理的。現如今,雖然航運業仍然在發揮重要作用,但國家的戰略新興產業集中在空天海洋、信息網絡、生命科學和核技術等領域,水運業并不是國家倡導的核心,因而應將重點集中在如何優化升級上,如何為戰略新興產業提供更好的水運服務上。在這樣的環境下,創造公平公正的市場、讓更多的主體參與其中、解決過往趕超戰略所積累的諸多制度問題應當成為重中之重。
[1] 林毅夫,我和張維迎在爭論什么,價值中國,2016-09-12
來源:謝燮(供職于交通運輸部水運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絕頂思維(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