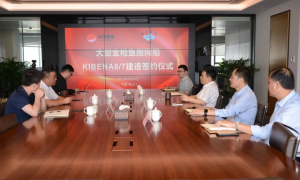以“讓石油重回供需平衡時代”為主題的新一輪多哈會議于4月17日結束。盡管有多達18個全球主要產油國參會,然而由于未能達成預期的凍產協議,國際油價隨之應聲下跌。對于國際能源市場而言,本輪多哈會議的結果似乎并不意外。作為產油大國的沙特早在會前就曾表示“如果伊朗不加入凍產,那么沙特也不會凍產”,而伊朗缺席本輪會議的舉動直接表明了伊朗并無減產意圖,因此本輪凍產會議的結局也就不難預料了。
科威特石油公司市場研究經理Haitham Al-Ghais 4月25日在阿布扎比表示,科威特計劃到6月份將原油日產量從300萬桶提高到315萬桶。然而,這一象征性的增產措施并沒有對油價上漲起到應有的作用,油價走勢由此變得撲朔迷離。未來國際原油市場供求關系將隨主要石油輸出國與石油進口國博弈的加劇及石油金融體系的改變而呈現出更為復雜的發展局面。
石油大國沙特態度
作為國際原油供應市場主力的沙特在石油方面的動作對于國際油價的影響毋庸置疑。據估算沙特石油開采成本約在每桶5美元以下,且依靠短途管線與海運結合的模式,沙特的原油輸出到出口終端的成本不超過每桶4美元。從這個角度來看,只要國際油價在10美元/桶以上沙特的油井就能繼續維持生產。
與沙特相比,委內瑞拉、墨西哥、尼日利亞等地區的石油多蘊藏于深海,平均開采成本在20~30美元/桶,將石油運輸到輸出終端的成本為4~5美元/桶,所以以委內瑞拉和墨西哥為代表的新興石油輸出國的石油實際生產成本可能接近40~45美元/桶。當國際市場上的原油售價低于這個價格時,越生產越虧損的局面將使這些新興石油輸出國大范圍減產。
同為石油輸出國的沙特面對連續18個月的低油價“面不改色”,只要國際油價不跌破中東地區的成本價,以沙特為代表的中東石油大國都不會有減產的壓力。由此可見,以沙特為首的中東國家對國際原油的定價有著很強的話語權。
解禁后伊朗入市影響
沙特的老對頭,同為石油輸出大國的伊朗在國際制裁初步解除后正積極恢復制裁前的石油生產與銷售水平。然而,運力的缺乏與金融制裁成為伊朗石油出口的兩大瓶頸。伊朗國家油運公司(NITC)曾經是全球最大的油運企業,擁有42艘VLCC、9艘蘇伊士型油輪和5艘阿芙拉型油輪,總運力達1600萬DWT。然而受制裁影響,目前伊朗國內現有的油輪普遍老化,需要進行現代化改裝后才能滿足現行的國際航運標準。據樂觀估計,目前伊朗國內能夠立即投放到國際航運市場上的VLCC僅有15~16艘,在不繼續增產的前提下也只能滿足目前50%的石油出口運輸需求。因此,伊朗的石油出口在未來3~5年內依然無法擺脫對國外運力的依賴。
不過讓伊朗感覺最為痛苦的還是金融制裁。盡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目前已放開與伊朗進行國際貿易的限制,然而依然沒有對伊朗開放美元金融系統。由于國際原油市場主要以美元進行計價和結算,這使得伊朗提升國際原油市場份額的戰略變得十分困難。與此同時,美元支付能力的缺乏也讓國外的油運企業與伊朗的交易變得非常麻煩,不少油運企業都不愿與伊朗交易。從這個角度來看,產油大國伊朗能夠投放到國際原油市場上的原油非常有限,伊朗的態度尚無法對目前的國際油價造成顯著影響。
石油進口國消費能力飽和
持續的低油價成為石油消費國和國際油運市場的重大利好。油價的暴跌極大地刺激了石油進口國的燃油消費,原油的運輸需求隨之大幅增長。后金融危機時代飽受運力過剩之苦的油運企業開始扭虧為盈,原油市場上充足的供應和亞洲地區對于能源需求的持續增長讓中東和亞洲地區的港口開始承壓。
受低油價刺激,中國煉油企業開始大量購入原油,年初中國主要港口的原油吞吐量迅速增加且平均增幅都在10%以上,青島港甚至出現了進口原油的油輪大量壓港,1個月內都無法靠岸卸貨的“壯觀”場面。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歐洲和東南亞地區。歐洲最繁忙的海港鹿特丹港出現了自2009年以來從未出現過的景象,平均每日等待卸貨的超級油輪在40艘左右,數量最多時達到50艘,這一數據是1年前的兩倍。
受大范圍油輪壓港影響,國際原油運輸成本開始上漲。根據國際原油交易的慣例,如果貨物未能在指定的時間卸貨,租船人不僅需要繼續承擔船舶日常開銷,還需要向船東支付數額不菲的滯期費,由此將導致VLCC實際使用成本高達12萬~15萬美元/日。對于石油進口國而言,這些能夠載運200萬桶原油的VLCC在港口每滯留一天就意味著原油采購的成本增加0.06美元/桶,對于尺度略小的蘇伊士型或阿芙拉型油輪而言這個數字將上升到0.08~0.11美元/桶。目前中東和亞洲地區的大部分港口或多或少都存在因擁堵而導致的油輪壓港問題,平均累計壓港時間都在30天以上,石油進口國為此而承擔的額外成本已達1.8美元/桶,如果再考慮這些油輪滯港期間船上載運貨物的時間價值這個數字將上升到2.1美元/桶。由此可見,由于原油需求旺盛而導致的港口擁堵已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石油進口國能源使用的總成本。
隨著全球原油消費能力的不斷透支,關于儲油空間不足的預警也不絕于耳。預計這一波行情過后,新開采的石油已經很難在國際市場上找到買家。從年初開始,不少能夠通過蘇伊士運河的油輪開始選擇繞行好望角或以更低的航速航行,以期在油輪航行的過程中能為船上的石油尋找到潛在的買家。而更多的油輪則選擇在港口附近拋錨,以等待港口儲油設施重新獲得接收能力后卸載貨物。隨著全球原油供應市場的進一步失衡,未來將有越來越多滿載原油的油輪加入等待卸貨的行列,國際原油運輸成本還會進一步提高,這將直接提升能源消費國的能源使用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全球的能源消費。
低油價時期大量新增的投機性原油采購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未來油價的上行壓力。與全球范圍內原油供應過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最近包括油輪在內的不少船舶在港口申請加油時都被告知受市場總體供應量的限制,港口的燃油供應商無法完全滿足所有船舶的加油需求。一些船舶由于無法獲得足夠的燃料而不得不選擇在錨地或港口停泊等待加油。受低油價的驅動一些燃油供應商開始加入原油投機行列,在低油價時大量囤積原油以期在油價上升時出售以獲得更大的利潤。這些投機行為讓本已撲朔迷離的國際原油市場形勢變得更加復雜。
石油貿易體系變化
國際貨幣金融市場對油價的影響也不容忽略。作為中東地區的石油輸出大國,伊拉克率先試圖脫離石油—美元體系,采用歐元與歐洲國家進行石油交易;非洲的石油輸出大國利比亞也開始在非洲推行以黃金進行石油貿易的清算。然而這兩個企圖挑戰石油—美元體系的國家最終為自己的冒險舉動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2014年年初俄羅斯吞并克里米亞并軍事干預烏克蘭的事件引發歐洲地區對俄的經濟制裁。然而讓美國沒有想到的是,俄羅斯率先與中國采用人民幣進行能源交易,稱霸國際能源市場長達45年之久的石油—美元體系第一次受到了實質性的挑戰。石油—美元體系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制裁俄羅斯的經濟基礎。然而,中俄貿易“去美元”的成功讓西方國家對于俄羅斯的制裁大打折扣。中國擁有俄羅斯目前所需的糧食與各類輕工業品,而俄羅斯則擁有中國所需的能源,理論上兩國貿易完全可以脫離美元進行。去年11月28日,俄羅斯央行正式宣布將人民幣納為俄羅斯外匯儲備貨幣。這意味著中俄貿易已全面擺脫對美元的依賴。
中俄能源貿易“去美元”的成功也讓伊朗看到了希望。由于無法進入美元金融體系,伊朗開采的石油目前還沒有真正進入國際能源市場。隨著未來伊朗石油產量的迅速增加,這批石油的動向成為目前國際原油市場最大的懸念。如果最終美元對伊朗完全解禁,則這批石油將進入石油—美元體系,新增的供應量將進一步增加油價下行壓力。如果長期無法進入美元金融體系,伊朗未來生產的石油就有可能徹底脫離該體系的控制,此時無論采用美元還是非美元計價的原油市場都將因供求關系的劇變而前途未卜。
長期以來,國際油價的變化一直牽動著航運業敏感的神經。通常而言,油價上漲將抑制世界經濟增長,進而導致航運需求減少;油價下跌,國際航運業就會出現完全相反的局面。然而國際原油市場的實際狀況一次次證明,每一次油價變化的背后都有深層次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原因,未來國際油價的變化依然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僅依靠市場供求關系的分析并不可靠。對于能源依賴程度較高的航運業而言,這一點是必須時刻牢記的。
來源:航運交易公報